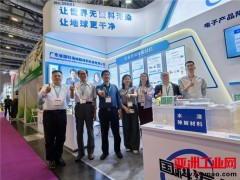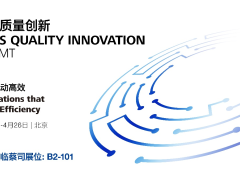属地管理并未优化监管职责
纵向体制对监管能力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判断一项事务是否应当垂直管理的主要标准,是其负外部性的溢出效应。食品药品安全具有跨区域流动性、全生命周期性等特征,不同于一般产品。
因此,从2001年开始,中国工商、质监、食药监等部门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体制,监管人员、经费、工作在省级范围内统筹。然而2008年之后,几个部门的垂直体制相继被取消,改为属地管理。
属地管理的目的是让地方政府真正担负起“总责”,然而政策在执行中出现异化。
一是监管职责“层层下压”效应。属地管理后,由于法律、“三定方案”、省级食药监局对各级食药监管事权划分并不一致,加之“上下一般粗”,即权责同构的行政体制,导致省市县三级监管部门职责边界并不清晰。
在最严问责的压力下,一些地方以属地管理为理由,把食品药品监管事权层层下放到乡镇市场监管所。市县两级不再从事监督检查或办理具体案件,但相应的检测、执法等监管资源并未随之下沉。这就意味着,基层必须包揽从小餐馆到大药厂的全部食品药品业态监管,给实际效果带来严峻挑战。
二是地方政府“扭曲执行”效应。尽管属地管理有利于落实地方政府责任,但并未真正激发其内生动力。地方政府的目标具有多元性和变动性,每个阶段关注的重点不同。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工作相比,食品药品安全很难进入优先政策议程。现实中,屡屡出现食药监管所人员被乡镇抽调,从事征地拆迁、市容整洁、大型活动保障等情况。
与此同时,产业发展与质量安全没有形成相互兼容的良性关系,食品药品监管在不少地方政府眼中依然是“花钱”的事,陷入“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的尴尬境地。在人员编制、机构数量、财政经费等硬约束下,地方保护主义并未完全消除。
超越模式之争的建议
2018年新一轮机构改革蓄势待发,具体到食药监体制改革,存在两大焦点:一是纵向体系垂直还是属地,二是横向机构单设还是综合。笔者就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机构设置差异化,给予地方一定探索空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大部门制要稳步推进,但也不是所有职能部门都要大,有些部门是专项职能部门,有些部门是综合部门。”这一表述强调了专业部门与综合部门的区分,要求实事求是地推进监管体制改革。
3 4 5 下一页> 余下全文page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