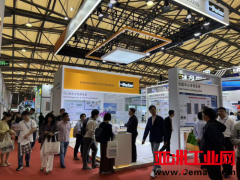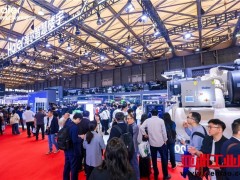——亚夫
新一轮工业革命可能导致就业市场分化,出现“低技能、低收入”和“高技能、高收入”并存的情况。应打破“低成本劳动诅咒”,克服因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对传统生产方式的过度依赖,以及对新工业革命的恐慌,摆脱劳动密集型生产范式,实现生产技术和人的全面发展。
要顺应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将政策重点引导到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路径上去。在资源布局上,要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技能—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过程变成促进高质量就业、提升人力资本结构的过程。
□张茉楠
新工业革命对全球就业的影响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数字技术、物理技术、生物技术有机融合,触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可植入技术、数字化身份、物联网、3D打印、无人驾驶、人工智能、机器人(25.780, 0.00, 0.00%)、大数据、智慧城市等将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重塑全球生产、消费、运输与交付体系,新产业、新业态、新经济随之应运而生。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的致辞中也多次提及中国的经济转型、新动能和传统动能的转换,并表示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历史性机遇。然而,机遇与挑战同样并存。根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一项报告,第四次工业革命将造成5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如果各国政府对此不采取行动,将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以数字化或3D打印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在5年内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内500万个工作岗位带来威胁,这也引发了一些国家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带来的结构性冲击的担忧。我们应该如何客观评估这种深层次的影响呢?
1.新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对全球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比较复杂
国际劳工组织预测显示,自2000年至2019年,低技能就业一直处于下降趋势,高技能就业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4年低技能和非常规的体力工作占全球就业总量的45%以上,中等技能常规工作占就业总量大约37%,高技能工作占就业总量大约18%。但是,世界不同地区存在很大差异。数据显示,2000-2013年期间,所有地区的低技能就业占就业总量比例都有所下降(发达经济体除外),减幅最大的地区是东亚和南亚,均减少了8个百分点以上。
发达经济体的中等技能就业在下降,被低技能职业部分代替。但是,中等技能就业创造的产值占全球经济的份额保持稳定。所有地区的高技能就业占就业总量比例都有所上升,增幅最大的地区是中东和南亚,分别增加了近6个百分点和5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新科技革命与新工业革命也可能导致就业市场的分化,出现“低技能、低收入”和“高技能、高收入”并存的情况。高水平的自动化和互联功能将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制造新的财富差距。瑞银集团在此次论坛上发布的白皮书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可能削弱新兴市场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发展中经济体将面临更大挑战,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政策,这次工业革命将加剧不平等。
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于前几次工业革命中机器与人的体力劳动之间的简单替代关系,它对劳动力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高度自动化的生产会导致简单劳动者失业;另一方面,智能化的生产又会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工作机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自动化生产为我们的判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自动化设备的广泛应用并没有导致大规模失业,原因是工业自动化所带动的投资及其就业创造效应完全抵消了资本深化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生产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更多是结构性的,即技能型工人对于操作型工人的替代。
2.长期看,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并不会导致大规模失业
事实上,到底如何评价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对人类的影响一直是一个复杂性难题。对科技进步与劳动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早在18世纪末期随着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就受到广泛关注。
迄今大多数学者认为,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短期会使失业增加,但从长期来看又可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可以认为在短期科技进步使得资本有机构成、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在长期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加速、不断产生新的产业和新的就业机会从而增加就业)。OECD基于其成员国200年的数据研究表明,创新、增长和就业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尽管短期内科技进步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相对于其巨大的创造效应可以忽略不计。
自工业革命以来,“机器替代人”的困扰始终伴随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在始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以及以福特制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都因为新机器的采用,出现了对劳动力大量失去就业岗位的担忧。但事实证明,机器在替代劳动者原有岗位的同时,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高,劳动者总能在新的行业、新的岗位重新就业。
在人类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出现大量失业问题的时间并不多,且大都是因为经济周期因素造成的,由机器造成的失业总是短暂和临时的。目前,随着工业机器人发展加速,各国制造业工业机器人装机数量大幅提高,又出现对工业机器人是否会大规模替代劳动者并产生失业问题的担忧,但实际上,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2000-2010年,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中国、巴西六个国家中,除日本,其余国家制造业机器人的数量都翻倍,而除美国之外失业率都有所下降,也即工业机器人的采用和普及在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引起失业率的提高。相反,工业机器人的出现和普及在很多国家是和失业率下降同步的。
我们以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具代表性的工业机器人行业为例。目前,从全球范围看,工业机器人的普及没有减少人类劳动者的岗位数量。工业机器人在全球制造业装机数量的快速提高的驱动力主要有三:一是人类劳动无法满足产品制造的高精度、高硬度和低成本要求;二是人类劳动无法适应生产环境和生产条件;三是制造业无法负担高额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前两个驱动因素并不会直接减少人类劳动者岗位数量,第三个驱动因素只在制造业企业无法承担人类高额工资时才起作用,如果工资上涨速度减慢或产品价格提高,工业机器人同样不会替代人类劳动者的岗位。
应对新工业革命需要升级劳动力与就业结构
国际经验证明,高级技术人才储备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能够真正发挥其价值的首要因素,高级技术人才缺乏也是影响第四次革命发挥作用的最大挑战。
1.我国面临劳动力市场长期严峻挑战
当前,人口红利下降、人力成本上升、人才结构矛盾等问题正在倒逼一些国内制造业企业以机器人换人。一时间,在机器人代替人工的表象下,“机器人将引发失业潮”、“智能制造就是‘机器换人’”等说法甚嚣尘上。因此,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长期和结构性影响需要深入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获益于人口红利。其中,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然而,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于2012年出现。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含不满60周岁)占总人口比重为69.2%,人数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比重比2011年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成为经济隐患。
另外,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也将对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统计显示,2014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亿人,占总人口的15.5%,高出2013年0.6个百分点,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1%。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根据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数字,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
再换个角度看,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竞争力压力不断加剧。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目前,中国制造业小时人工成本约为3美元,而美国制造业小时人工成本在35美元左右,从数量看,我国仍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但从发展趋势看,2004-2013年,我国制造业小时人工成本增长超过200%,年均增速超过10%;而同期,美国增长幅度仅为2.7%,年均增速不足3%。
而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却在放缓。从绝对量来看,目前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不足美国的10%,而在高端制造领域,美国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20倍以上。从增长趋势来看,过去10年中,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低于制造业工资成本增幅;而同期,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接近5%,高于劳动力成本增长速度。因此,整体制造业的竞争压力正在不断加剧。
2.劳动力结构及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严重不匹配
从一般制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的转换,整个社会对从事单纯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者的需求量相对减少,而对人力资本、R&D、技术进步等知识资本的要求大大增强。用人力资本、知识(教育)资本等来抵消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经济增速的下滑,并提高国民财富和经济增长质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随着我国产业的不断调整和升级,对技术工种知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以长三角为例,近些年长三角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出现“高级技工荒”的现象。据统计,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的120万家企业中,技师和高级技师的缺口高达68%。江苏的高级技工比例虽然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高级技术人才比例也只有8%,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40%。随着新工业革命的到来,不断涌现的新兴产业对技术人才的素质要求将更高,这一缺口预计还会进一步扩大。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